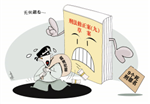
一、何谓“职务”
(一)职务与职权
《现代汉语词典》将“职务”一词解释为“职位所规定应承担的工作”。从行政法的角度讲,职务是权与责的统一,是为了行使国家、社会的管理职能而设置在各种 行政组织中具有法定权力和义务的国家公职。职权是职务所赋予的权力,职责是担任一定职务应尽的责任,职权是职责的外化。同样,公司企业及事业单位中的某些 职务虽然不具有国家、社会的管理职能,但是也是职权与职责的统一。可见,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职务”是广义的,在贪污罪中的“职务”与职务侵占罪中的“职 务”没有本质区别,两罪的区别仅在于是否行为主体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
经上文分析,笔者认为职权是职务的下位概念,是由具体职务派生出来的权力。职权是权力主体依法作出一定行为的资格,是权力的特殊表现形式。笔者认为,贪污 罪中“利用职务便利”往往表现在利用职权的方面。刑法将某类型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旨在保护一定的法益,贪污罪所重点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 性。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由职责与职权统一构成,其中职责是对职务的约束,约束职务主体规范自己行为积极履行某种责任。显然,这种职责的本意在于对己约束, 多是负担性的义务,往往不涉及利益。当这种职责没有被遵守时就会带来秩序的混乱,所以侵犯职责的行为往往表现为不履行职责,或者说是不作为,这种职务上不 履行职责的行为是典型的渎职行为。另一方面,职权是权力的一种,可以实现某种利益。所以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理解为谋取私利不合法运用职权侵吞、 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危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行为。
(二)职务与公务、劳务
国家工作人员就是指从事“公务”的人员吗?贪污罪中的“职务”是指公务吗?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公务”的理解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 它是指“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 另有观点认为“从事公务是依法所进行的管理国家、社会或集体事务的职能活动。” 此外, 还有观点认为“从事公务就是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 对于上述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以是否从事公务来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方法已为法律认可。当然,事实上从事公务是界定国家工作人员的实质性要件,而形式 上是否获得委派或授权也是界定主体身份的标准之一。根据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要有国有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的委派,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应有法律的规定就可以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如此看来,贪污罪中的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成立需要符合实质性要件即 稳定性地从事公务活动和形式要件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人员或受相关单位的委派或有法律的授权。
对于第二个问题,《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笔者综 合上述观点认为,公务应当指公共事务, 具有管理性, 同时具有代表国家性, 它是一种国家管理性质的行为。单纯劳务是相对公务而言的, 它不具有管理性, 是具体的劳动力的付出。从职务概念的内涵来看, 职务是指工作中所担任的事情或职位所规定应该担任的工作, 职务的范围当然包括公务和劳务。而单纯的劳务即体力劳动不具有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力,劳务虽然可以产生是对公共财物的占有,但是这种占有是为了完成搬运、加 工等工作的必要前提,不具有控制管理权力。其实不难发现职务的外延较为宽泛, 以至于贪污罪主体要件从事“公务”的要求与客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要求产生了矛盾。笔者认为应当用贪污罪主体要件的要求对“职务”概念的外延进行限 制,所以贪污罪的“职务”不包括单纯的劳务。对比而言,刑法第271条第(1)款对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则规定为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显然不仅包括其 公司、企业或单位的董事、经理、领导,而且包括其他管理人员和劳务人员,那么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劳务人员(包括国有企业、事业或其他单位的劳务人员) 利用劳务之便侵占本单位财物的行为也应归入其中。因为贪污罪涵盖的仅仅是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对于从事劳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单 位财物的行为应以职务侵占罪论处。
二、何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一)学界的不同看法
1.有学者认为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其职权范围内的合法条件,而不是利用与其职权或者职责无关的条件,如因工作关系熟悉作案环境,或者凭借工作人员的身份,较易接近作案目标或对象的方便。
2.有学者认为贪污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直接利用本人职务上的权力,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利用本人主管、经管财物的职务的便利条件;另一种是担任其他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执行公务而临时经手、管理公共财物。
3. 第三种观点认为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仅包括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范围内的权力所形成的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有利条件,而且包括与职权无关的仅因工作关系对案件环境比较熟悉,凭借身份便于进出本单位、易于接近作案目标的方便条件。
4.也有学者认为贪污罪和贿赂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放在一起考虑,认为包括直接利用本人职务所造成的便利条件,也包括间接利用本人职务造所成的便利条 件。所谓间接利用职务便利指国家工作人员不是直接利用本人的职权,而是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 利益。所谓间接利用本人职务上便利就是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从表面上看是通过第三人的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但从实质上看,行为人是利用了本人职务而 产生的制约关系,这种制约关系可以左右和影响第三人的利益,使之就范,否则就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
(二)对上述观点的评析
笔者认为,上述这些关于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都存在一些不够准确或者没有完全把握立法本意的问题。
第一种观点强调贪污罪的职务上的便利其职务必须是合法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设立贪污罪旨在保护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如果这种职务本身不合 法,也就根本谈不上廉洁性的要求了。但是现实中的案例往往是复杂的,如果行为人采用欺骗的手段获得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和相应职务,并利用该职务便利侵吞 公共财物,不定贪污罪显然有违常理。笔者认为,在要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职务合法性时,只能是现行存在的职务的合法性而且合法性也只能是形式上的合法性。 对于上述案例中,虽然行为人存在欺骗手段,但是经过组织任命或者选举考察,该职务在形式上就具有了合法性。对外,这种职务就具有了公信力,其职务权力行使 产生的法律效果与其他合法取得的职务没有区别。
第二种观点将临时经手公共财物的便利看做是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涉及到关于职务行为有无时间限制的问题。有些学者主张从“职务上的便利”的 内涵来说,职务、职权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如果行为人本来不具有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职权,只是偶然一次接受委托经手公共财物,则不能认为其具有 “经手”公共财物的便利条件,从而将其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认定为贪污罪。 笔者同意此种观点,职务是“职位所规定应承担的工作”,可见职务是基于职位产生的,贪污罪中的职位往往是管理国家、社会公共事务的职位,为了维护社 会公共秩序的稳定,这些职位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可能是一次性的。即使行为人接受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的委托,从事一次性的经手公共财物的活动时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也不能认定为贪污罪,而应当根据其手段认定为侵占罪,盗窃罪、诈骗罪等普通犯罪。
第三种观点显然扩张解释了贪污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不符合立法本意。这里就要提到一道很有争议的司法考试试题。2008年司考卷二第18题为 “某国有公司出纳甲意图非法占有本人保管的公共财物,但不使用自己手中的钥匙和所知道的密码,而是使用铁棍将自己保管的保险柜打开并取走现金3万元。之后,甲伪造作案现场,声称失窃。关于本案,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当年司法部公布的正确答案为C.甲将自己基于职务保管的财物据为己有,应成立贪污罪。 很多学者认为通过题干描述甲未使用职务上的管理、经手的便利条件,不应认定为贪污罪。
第四种观点存在严重偏差,将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混为一谈考虑。虽然在《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利用职权或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解释为包括“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如单位内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上隶 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但是这是在“关于受贿罪”的语境下对“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解释,不能将其直接套用于贪污罪。根据刑法第388条,间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构成受贿罪,而笔者认为贪污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仅限于直接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无论是在纵向的上下级的领导关系,还是横向的制约关系都可以归入到“管理、主管、经手”的范畴。事实上,这也被司法解释所确定。1999 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中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对于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解释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指利用职务权利和地位所形成的主管、处置、经营、经手公共财 物的便利条件。”主管,主要是指本人虽不具体管理、经手公共财物,但负责调拨、处置及其它支配公共财物决策权的职务活动;管理,是指直接负责保管、处理及 其他使公共财物不被流失的职务活动;经手,是指领取、支出等经办公共财物的职务活动。
三、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评析
(一)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比较
刑法第271条规定职务侵占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第382条规定贪污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骗取、窃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似乎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的行为手段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学者认为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在客观行为手段上没有实 质区别,亦即职务侵占罪中的“非法占有”即“侵占”应作广泛的理解,与贪污罪中的“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手段”含义一致。笔者同意上述观点,上述观点不仅符合立法本意,而且从犯罪类型上看,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都是普通侵占罪的特殊化。侵占行为实质指将代为保管的物据为 己有或将遗忘物、遗失物据为己有拒不交还的行为,无论行为人采用的是掩人耳目的骗取、窃取还是其他方式都不能掩盖这种将应经占有之物据为己有的本质。至于 手段的表现形式是不可能被立法穷尽的,也没有必要具体规定。
(二)因身份享有某种权力,行使权力时与单位财物发生关系,利用这种关系而非法占有财物是或否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例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甲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甲擅自涂改医药费收据,将多报销的钱财侵吞,那么甲是否构成贪污罪呢?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分析该行为有没有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如果根据政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普遍享有公费医疗的权利,那么甲虚报医药费的行为是利用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而不是利用甲的具体职位所 应包含的职权。其次,显然这笔公共财物也不属于甲的主管、管理、经手范围,不应该认定为贪污罪。
笔者认为,在具体个案中考察贪污罪的“利用职务之便”应涵盖以下内容:第一,行为主体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贪污罪是真正身份犯,身份的有无直接影响罪的成立。第二,行为是否与行为人的职权存在实质的联系,是否利用了对公共财产的主管、管理、经手等便利条件。第三,行为人的职务是否具有现实性和稳定性。